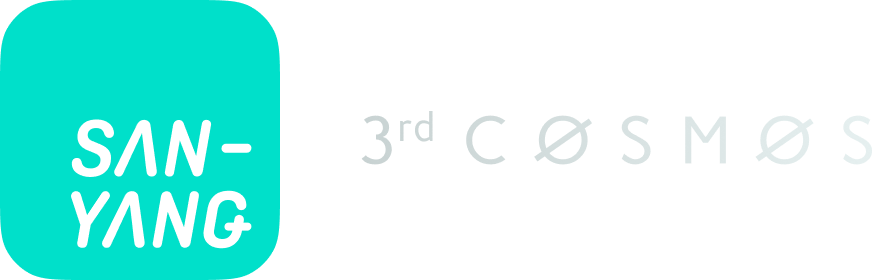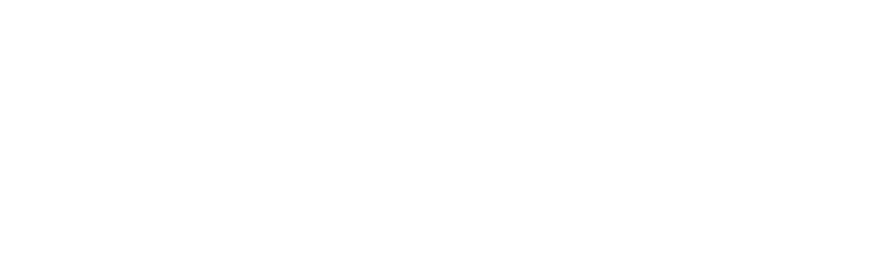玛格丽特和三得利

2015年第一天凌晨,在一家小酒馆内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分享了老板赠送的香槟、蛋糕,倒数着进入了新的一年。同时,也第一次品尝了新基友推荐的玛格丽塔。
要知道,平日至多只喜欢随意喝些三得利(或是其它什么可以很容易从便利店买到的品牌)啤酒的我,在带着轻蔑的眼神喝了一大口「柠檬水」后,开始有些后悔之前的诳语。玛格丽塔入口后的第一感受是淡淡的柠檬香,貌似清淡而寡味,但随后就会露出她的烈酒本性,你会感谢抹在杯口一圈的盐帮你缓和了突如其来的刺激。在一杯快要见底之时,就有了期待已久的感受了。
我并不嗜酒,但仍然喜欢习惯性地问对方有酒喝吗?因为自从第一次体验到微醺的感受后,我就爱上了它,甚至有点像中的 Rajesh 一样对这种感觉有些依赖。
第一次微醉是第一次见尺子君的那次,当然,是一个社群聚会。不知是多少啤酒下肚(应该不会太多),我起身去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是在直线前进,而是不由自主地晃荡起来,随之晃荡的还有自己的心情——不知从而来的快乐。我拉着尺子君的手,说「你的手真好看」。
仿佛这一切的话都脱口而出,仿佛往日里道德伦理或是性格文化之类的一切束缚都不存在了,我可以无所畏惧地「我口诉我心」。那时,我认为酒就是用来壮怂人胆的灵丹妙药,它可以让你疯狂,让你说平日不敢说的话、做你平日不敢做的事。
第二次是在尺子君的宿舍,去之前我拎了6罐啤酒,没有特別的原因,我只是觉得这会是一个需要长谈的夜晚,需要一些酒精来帮助我们开拓思绪。尺子君勉强喝了一罐,我不记得喝了几罐,直到出现了第一次的奇妙感受。后来,尺子君默默在手机萤幕上敲出了一句话,递给了我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吓趴在了地上。当然,这是酒精的缘故让肢体动作显得夸张了。那个夜晚,我们睡在不同的床上,虽然我上半夜因为担惊受怕没有敢睡,最后也还是太太平平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一次,我又更新了自己对于酒的理解,那就是它固然可以帮助我壮胆,但它替代不了我的思考,我仍然会保持著理性,在最大的程度上。
因为昨晚的折腾,直到今早11点才起床,一个小时后的手机萤幕上跳出了联络人的生日提醒,看了一眼,我知道尺子君的生日要到了。
似乎从来没有为尺子君过过任何一个生日,又或许曾经努力地想要忘记,因此能够记得的和他的故事,也就是在报社保持著一种微妙的默契、听他说他在各地采访又见到了什么明星、第一次在南京拜谒国父是和他在一起、他用他的「社会现实情怀」来暗讽我「高尚的道德情怀」、在大半夜因为和他的争执而一气之下报考设计学研究生……我只记得那时自己刚刚学着去做一些独立的思考,於是觉得尺子君是如此的 simple 以至 sometimes naive,我惊呼天吶,我怎能和一个如此世俗的人在一起!我要告別他!
这就是玛格丽塔最初柠檬香般的错觉。今日想来,我又何曾理性?
如今我在墙上挂了三位人物的照片,分別是 Henry Van de Velde、Tim Cook 和孙中山。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内有著不同的卓越贡献,但这三位导师身上都散发着同一种光辉——理性。
和尺子君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披着「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外衣,用著非理性的脑袋去说着非理性的话、做着非理性的事,现在想来,其实尺子君确实是更对一些的。其实并没有高尚和不高尚,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我曾经会因为「尺子君」的现实主义而远离他,今日却愿意与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复旦老猫交往,对待同样的选择,有著尊敬与不尊敬两种态度,我想背后的因素就是理性与否。一是对方的理性与否决定了你是否尊重他,二是自己的理性与否决定了你所表达出的态度。
当然,理性的获得并非容易。如果说和尺子君在一起的那一年正是因为自己出于非理性目的而做出的决定注定了最后的失败,那我非常震惊在过去的一年我竟惊人地重复了这种非理性,当然我不是说我要这么急于预言最后的结局,而只是说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失败,那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了。非常惭愧,在很多时候,我依旧不能保持著理性。
走出小酒馆,凌晨1点多的风特別大,微醺的感觉没多久就被风吹散了,我还是那个胆小、懦弱的我。今年是大家都愿意走出家门跨年了吗?大半夜的马路也被汽车挤得水洩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