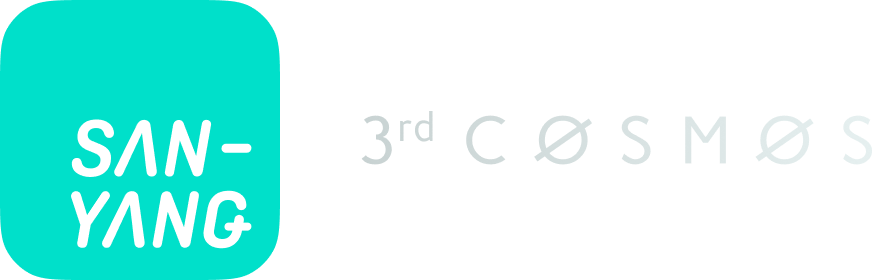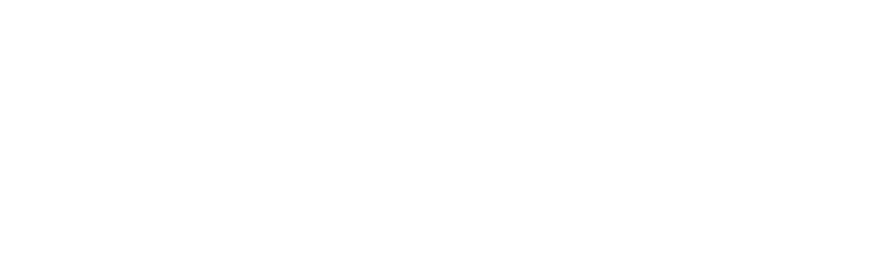落在好土里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马太福音 13:3-8
这是圣经中耶稣对听他讲道的民众所说的比喻,也是基督徒常常互相勉励的教导。即便对于不是基督信仰的人而言,这也是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语。
我们常问「为什么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 我们的一生中听到太多的教导和劝诫,然而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里面、翻转我们生命的是少的。
圣经说要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让所听到的道进入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些道才有了生命和意义,它就要在我们的人生中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来。
最近,我基于这个主题,创作了一副主题为「落在好土里」的插画。
《落在好土里》
我很希望这样一副基于圣经故事创作的图画可以被更多人所看到,我在网上批量购买了画框,将图画高清列印出来,一副一副手工将他们组装成为了挂画。我透过社群售卖这幅作品,并且清楚地告知顾客,每幅挂画的真实成本和利润,我承诺售出挂画的全部利润将捐献给教会用于福音事工。
手工制作和打包每一副挂画
出乎我意料的是,透过网路的传播,和教会朋友的热情转载,我收到了大量的挂画购买需求。有很多教会朋友一次性购买十幅、二十幅用来赠送亲友。这段时间,我的宿舍变成了施工现场和库房,细心打包每一副需要寄出的挂画。
在此之外,这幅画作也被学院所注意到,正在进行中的四平社区更新项目邀请我将这幅画作改制成为更大的尺寸,装饰在社区的公共空间中。
楼道装饰前后
透过这幅画,我并不期望成为某种信仰的传播者,只要这幅画能让收到它的人感到温暖,这就足够了。
页面内使用到的音乐版权信息《好土 Have the Glory (I Wanna Be the Good Soil)》詞曲:Jon Thurlow / 中譯詞:趙治德©2019 趙治德 / admin by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宗教改革500周年米兰游行见证
2017年是基督教宗教改革的50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在世界各地陆续展开。米兰的纪念游行从米兰大教堂出发,一路走过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街道。我系上牧师在起点处发放的红色丝带,跟着人群缓缓向前,感受着在中国难能体验到的表达方式。
拜谒维尔德先生之墓
在学习近现代设计史的时候,许多的设计前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一位就是维尔德(Henry van de Velde, 1863-1957)先生。
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虽然已有了现代主义意识的萌芽,但装饰艺术仍然深入人心、成为惯性,维尔德先生自然也是一位好手。维尔德先生擅长使用曲线,但他更理性地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未来,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他会克制自己内在艺术的冲动,而是追求理性认为对的设计。
更难能可贵的是,维尔德先生更是反对标准化给设计带来的限制,前瞻地预告了现代主义思潮会给设计带来的负面冲击。
我所有工艺和装饰作品的特点都来自一个唯一的源泉,即理性,表里如一的理性。Henry van de Velde
在3年前,我默默许下心愿:如果有机会去欧洲留学,一定要去这位带给过我感动和动力的精神导师墓前拜谒。
维尔德的墓并不好找,寻遍网路都没有什么收获。最终通过电邮联络上了维尔德先生线上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获得了详细位置和前往方式。维尔德先生及其夫人静静地长眠于比利时佛兰芒-布拉班特省的一处小墓地,需要火车转公车,再步行相当长一段路才能到达。为了不打扰先生安眠,就不在此披露详细地址了。
维尔德先生长眠于一处非常普通的小墓地
中国人有扫墓的习俗,通常会带着一些祭品去拜谒先人。维尔德先生是比利时人,我确实也不太清楚带什么样的祭品才比较合适。最终,带着从布鲁塞尔买的巧克力和啤酒,以及赤诚的心,坐在维尔德先生墓前告诉先生我对于设计的思考和心得。
向维尔德先生报告设计心得
啤酒和巧克力
维尔德先生除了带给我设计上的启发,更展现了不论环境如何,始终敢于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设计道路的勇气。作为设计师,我有自己的梦想和渴望,也有自己的迷茫和胆怯。愿我的未来能带着维尔德先生的勇气前行。
服务设计学习的日常
这两年「服务设计」这个词在业界火了起来,仿佛有当年人人都在说交互、说用户体验的势头。这篇我用同济大学的服务设计工作坊课程来介绍以下服务设计学术派的日常。
给岁月以文明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这是刘慈欣《三体》中的一段话。我有一些话想对2016年说。
服务设计和产品服务体系设计(PSSD)的区别
咚咚咚(敲黑板),准备记知识点!
最近就服务设计和产品服务体系设计(PSSD)的区别的问题请教了米兰理工大学的 Davide Fassi 教授,Fassi 教授的意思如下,供诸君参考:
SERVICE DESIGN
It means to design strategy, system, considering touch points, stakeholders, user journey. It is a defined framework where different competences could be put into (interaction designer, interior designer, visual communication etc.)
PSSD
It is not only service but it includes a physical evidence (the hardware part of design). So a PSSD designer has ...
不去远方,哪来的平凡
"难道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会消失於这个世界上,我也会骑着一台 1000CC 以上摩托车,当人们问我去哪儿的时候,我忍著恶心,告诉他们,远方。"
这是韩寒在《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的话,大二读到它时,我把他抄了下来。当时触动至深,因为心中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愿望,和不能迈出门但至少打开一扇窗的愿望,被韩寒的这些文字引起了共鸣——我要去远方,我要离开流沙,因为当我挣扎著跳起之后,发现我原来不是一株植物,而是一只动物,这帮孙子骗了我二十多年。
要去远方的愿望从初中就开始萌动,但终究只是被蒙着眼睛的萌动。虽然我常常会去写一些渴望探索的文字,而实际上仍然在角落里彳亍。从未真正迈向远方,又怎可知远方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致。讽刺的是,因为这些颂扬探索的文字常常被鼓励、被视为独立思考、被视为终于成长,因此我逐渐地以为我已经去过了远方,我已经探索过了他们所说的另一个世界。
你要去远方,会有一种力量鼓励你、支持你,同时将你拉扯住,用一种声音告诉你、让你相信,你已经去过。其实,这样,和连一扇窗都懒的开的人没有任何区別。
没有办法描绘远方是什么样子,可能它会令你痛苦、令你不适,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的吉普车(或是汽油车)将你带到了可以看到 NT3M5P(卫星)发射的大漠,然后看到你朝思暮想的卫星发射失败在空中爆炸,而你的吉普车又被人开走了,在那样的荒原,你是什么感受?
在远方,一定是要失去理智的,就如同认为呆在角落里的人是神经病一样,不过是一群神经病嘲笑另一群神经病。但正因为在角落里做神经病太久了,才学会了在角落里生存的法则,你也一定要去远方,做彻彻底底的神经病,这样,你才能学会远方所要教给你的东西。在路上,千万忘记「优雅」两个字。
如果说之前韩寒的书是说去远方的故事,那么《后会无期》的韩寒,已经从远方回来了。
平凡之路是给去过远方的人准备的,而留在原地和以为去过远方的人得到的是「平庸」。换言之,平凡之路只有回到平凡,而从没有直达平凡。它是原点,它绝不是原点。
在思考的日子里思考,在该去远方的时候,请一定迈出步去,別总想着「平凡」,因为去远方的路实在太漫长,你还没有走到。
玛格丽特和三得利
2015年第一天凌晨,在一家小酒馆内和一群陌生人一起分享了老板赠送的香槟、蛋糕,倒数着进入了新的一年。同时,也第一次品尝了新基友推荐的玛格丽塔。
要知道,平日至多只喜欢随意喝些三得利(或是其它什么可以很容易从便利店买到的品牌)啤酒的我,在带着轻蔑的眼神喝了一大口「柠檬水」后,开始有些后悔之前的诳语。玛格丽塔入口后的第一感受是淡淡的柠檬香,貌似清淡而寡味,但随后就会露出她的烈酒本性,你会感谢抹在杯口一圈的盐帮你缓和了突如其来的刺激。在一杯快要见底之时,就有了期待已久的感受了。
我并不嗜酒,但仍然喜欢习惯性地问对方有酒喝吗?因为自从第一次体验到微醺的感受后,我就爱上了它,甚至有点像中的 Rajesh 一样对这种感觉有些依赖。
第一次微醉是第一次见尺子君的那次,当然,是一个社群聚会。不知是多少啤酒下肚(应该不会太多),我起身去上厕所时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不是在直线前进,而是不由自主地晃荡起来,随之晃荡的还有自己的心情——不知从而来的快乐。我拉着尺子君的手,说「你的手真好看」。
仿佛这一切的话都脱口而出,仿佛往日里道德伦理或是性格文化之类的一切束缚都不存在了,我可以无所畏惧地「我口诉我心」。那时,我认为酒就是用来壮怂人胆的灵丹妙药,它可以让你疯狂,让你说平日不敢说的话、做你平日不敢做的事。
第二次是在尺子君的宿舍,去之前我拎了6罐啤酒,没有特別的原因,我只是觉得这会是一个需要长谈的夜晚,需要一些酒精来帮助我们开拓思绪。尺子君勉强喝了一罐,我不记得喝了几罐,直到出现了第一次的奇妙感受。后来,尺子君默默在手机萤幕上敲出了一句话,递给了我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被吓趴在了地上。当然,这是酒精的缘故让肢体动作显得夸张了。那个夜晚,我们睡在不同的床上,虽然我上半夜因为担惊受怕没有敢睡,最后也还是太太平平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一次,我又更新了自己对于酒的理解,那就是它固然可以帮助我壮胆,但它替代不了我的思考,我仍然会保持著理性,在最大的程度上。
因为昨晚的折腾,直到今早11点才起床,一个小时后的手机萤幕上跳出了联络人的生日提醒,看了一眼,我知道尺子君的生日要到了。
似乎从来没有为尺子君过过任何一个生日,又或许曾经努力地想要忘记,因此能够记得的和他的故事,也就是在报社保持著一种微妙的默契、听他说他在各地采访又见到了什么明星、第一次在南京拜谒国父是和他在一起、他用他的「社会现实情怀」来暗讽我「高尚的道德情怀」、在大半夜因为和他的争执而一气之下报考设计学研究生……我只记得那时自己刚刚学着去做一些独立的思考,於是觉得尺子君是如此的 simple 以至 sometimes naive,我惊呼天吶,我怎能和一个如此世俗的人在一起!我要告別他!
这就是玛格丽塔最初柠檬香般的错觉。今日想来,我又何曾理性?
如今我在墙上挂了三位人物的照片,分別是 Henry Van de Velde、Tim Cook 和孙中山。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和时空内有著不同的卓越贡献,但这三位导师身上都散发着同一种光辉——理性。
和尺子君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披着「独立思考」、「批判精神」的外衣,用著非理性的脑袋去说着非理性的话、做着非理性的事,现在想来,其实尺子君确实是更对一些的。其实并没有高尚和不高尚,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我曾经会因为「尺子君」的现实主义而远离他,今日却愿意与坚守着共产主义的复旦老猫交往,对待同样的选择,有著尊敬与不尊敬两种态度,我想背后的因素就是理性与否。一是对方的理性与否决定了你是否尊重他,二是自己的理性与否决定了你所表达出的态度。
当然,理性的获得并非容易。如果说和尺子君在一起的那一年正是因为自己出于非理性目的而做出的决定注定了最后的失败,那我非常震惊在过去的一年我竟惊人地重复了这种非理性,当然我不是说我要这么急于预言最后的结局,而只是说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失败,那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了。非常惭愧,在很多时候,我依旧不能保持著理性。
走出小酒馆,凌晨1点多的风特別大,微醺的感觉没多久就被风吹散了,我还是那个胆小、懦弱的我。今年是大家都愿意走出家门跨年了吗?大半夜的马路也被汽车挤得水洩不通。
首论可穿戴设备
从昨晚的一个真实的噩梦说起:若干年后的苹果已是黔驴技穷,因为革命性的科技始终没有出现,因此要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创新就势必面临诸多勉强。有一日,苹果低调宣布开发了一款新产品,我有幸受邀见证,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他们剖开一个人的腿肚子,将一个电子设备植入其中,然后血淋淋地缝起……
除了从梦中惊起,难以置信地反问这难道会是苹果的作为?我还陷入了这样一个思考:科技的进步究竟需要使用者承担起什么样的代价?
穿戴式设备无疑已成为当下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是诸多资讯厂商正发力争夺的未来市场。因为穿戴式设备进一步将人与科技、资讯联合起来,为未来生活构建了无数可能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会是未来科技的呈现方式。
穿戴式设备其实早已在各类科幻电影中大出风头,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在脑袋中呈现这样的画面:一位步履矫健的商务精英,透过他电子眼镜的一角获知了一封新邮件的到达,於是,当他在桌边坐下时,他就可以立即进行回应了,当然,这一切可以直接通过口述完成。忘了一句,就是当他在完成上一个动作的同时,他可能在期间顺便回了几条简讯、拨打了一通电话……
我们都知道,包括目前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手机在内,当今的移动式终端的根本目的是资讯的交互,即我们使用的实质,是无数的字元资料的交换,而我们对于终端存在形式的不断探究,本质上是在回答怎样更好地交互。
变小的手机让我们不再需要扛着板砖出行,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而不断普及和便於制造的本身,则降低了我们进行资讯交互的门槛。当终端可以更好地同我们的身体结合,我们便有了更高效率的交互,也就更接近了终端的本质。
苹果的 iPhone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是因为它达到了怎样的工业设计的造诣,也不是因为它开创了怎样的商业模式,在今天这个话题的角度上来说,是因为它开创了更为自然、更接近本质的交互模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谁可以创造出比现在更接近本质的交互,谁就成为下一个时代的王者。
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让资讯脱离特定的介质形态而呈现,我的意思是我们想要呈现资讯,仍然必须为它创造一块「萤幕」;我们目前也没有个隔空探测的本领,我的意思是我们想要认识使用者,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产品和使用者呆在一起。
于是,穿戴式设备要登上历史舞台了。我相信现在距离我们能解决上面两个问题还有相当久远的年代,而这么一段历史时期内,业界不能无所作为。穿戴式设备虽然就整个发展史而言将起过渡作用,但就当下而言,它是主角。我们能够让资讯离人们更近,同时我们可以做到过去传统设备所做不到的——离人的身体更近。
当然,虽然不能无所作为,业界也不能为所欲为。伟大的现代主义导师凡·德·威尔德告诉我们「技术是产生新文化的重要要素」,在划时代的技术诞生之前,我们只能立足当下,像微软那样奇葩地去做未来式的设计语言,虽然值得尊敬,但是会死掉的。
穿戴式同作为植入式的最终形态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认为某款设备是可植入的,那意味着这款设备已接受了世界级的安全检验,与此同时,它也已经通过了社会关于这个问题的伦理检验,换言之,这款设备是「可信的」。它将作为人的一部分而存在,或许人的某些行为与其直接相关……这样一款设备是不容易出现的。
因此,至少在目前、在我所生活的背景和年代之下,穿戴式设备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是供「穿戴」的,也就是说可以想穿了就穿、想戴了就戴,不想穿了就脱、不想戴了就扔,想换了只要条件许可随时能换。至於植入人体,这不是穿戴式设备的许可权,作为一个人类,秉持自我尊严的底线,要拒绝这些电子设备侵入我们的身体和大脑。穿戴式设备应当找准自己的定位,用户也要把握对穿戴式设备的正确认识。
对哦,为什么导航系统都是女生?
刚阅读到蔡志浩先生的一文《为什么卫星导航系统都是女生?》,于是,也有了一个感叹,对哦,为什么卫星导航系统都是女生?
这对于业界或许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且对于越来越发达和追求个性化的科技而言,这个问题也不将是一个会继续被讨论的问题——因为将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人声可供选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大多数的电脑或其他智慧设备只有,或者默认使用的是女性发音。
面对这个疑问,许多人会不假思索的说,因为女生的声音温柔嘛,电脑一个大机器,冷冰冰的,能有女生说话才可爱嘛。
确实,如果你去便利店,有一男一女两位服务员,或许大多数人会倾向于选择女生(当然排除被长得像彭于晏一样的男生吸引)。对于机器,这个没有外貌等因素作为考量的东西,而言,这一倾向会更明显吧。
而如同蔡先生所言,「机器的声音不只是声音」。特別是在未来,这些越来越聪明的机器在我们生活中会更倾向与扮演伙伴的角色,甚至是全天候的伙伴。这就是说,在我们紧密、沉浸式地与这些机器发生交互行为的时候,我们将淡忘他们只是模拟人类智慧的机器的事实,而将其视为一个拥有智慧的生物。
智慧设备内在的交互特性,不仅在现在赋予了他们以人一样的情感,甚至在未来将会更具有社会角色的属性。
对于著名电影影响论(「1968 年的经典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杀掉几乎所有船员的人工智慧电脑 HAL 9000 的声音是男性,之后很多科技公司都避免在产品中使用男性的声音。」),我认为也许会有些夸张,事实是电影是人们既有观念的反映,而非电影导向。
无论如何,我确信,各大科技公司的程式员们而言,以现在的技术为支撑编写出的这些软体,大都服务於广泛用户,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使用一个最具普适性的选择——女生。待到未来,我们有能力去细化我们的产品,去针对不同人群、不同服务目的而打造智慧产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那些嗲嗲地对流氓说「不要这么做哦」的女生机器人说不。